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黑格尔的有论,抱歉出于我个人原因拖更了两周。
黑格尔在这里写了几版序言,然后第一版序言里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但是后来这样的关系改变了,我们接下来会主要解释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在最开始在写作精神现象学和第一版逻辑学的时候,精神现象学它还是作为逻辑学上的一个形而上学,即它还是体系的第一部分;但是后面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因为我们在哲学全书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哲学全书里面逻辑学自己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理解整个精神现象学,它对于意识和对象的关联这样一种表象性的批判。这样一种表象性认知方式的批判后来那一下子被整合到了逻辑学,也就是整合到了客观逻辑里面。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哲学全书的导言里面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里,它其实已经承载了整个的对表象性认知方式的批判,这就是为什么逻辑学它不再需要以一个在先的导论作为引导向它的体系的第一部分。这样的话,体系的第一部分直接从逻辑学开始就就已经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版,然后其实黑格尔的序言它是不太好读的。因为他的序言已经涉及到了许多对于整体性的理解方式。我们往往要彻底的内在的就是阅读过黑格尔的整个文本以后,才会才会更好的理解他的序言,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你们不要以为序言是好读的,就无论是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也好,还是现代的但是又非常古典的思想家,比如说德勒兹他们的序言本身就是不太好理解。
我们今天把序言讲完,讲完以后我们来讲整个逻辑学的一个存在论部分。
序言其实有两版的,两版序言是不太一样的,我今天会先给各位讲一下两版序言的一个区别,讲完以后我会讲导论,然后讲导论的时候我会讲的稍微快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看开端问题,所以我今天尽可能的以一种比较比较迅速的方式带大家把这样几十页给过一遍,然后我们后面就可以进入到逻辑学的主题里面。
大约近25年以来,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这里经历了完全的改变, 精神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时代也已经通过自己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立场。 但迄今为止,这些东西对于逻辑的形态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然后这里你会看到一个所谓的“近25年”。这里的近25年,其实就指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为止的一个时间。所以有本哲学史的研究就是讲的哲学的25年,也就是说他会把哲学就视为是内在的25年的一个演变,这其实就和黑这里的一个说法是有关的。我们会看到“近25年来”,哲学思想的一个变化其实也就涉及到了我们整个现代思想或多或少已经压抑的一个部分了。
我们现在思想谈到变化的话,往往谈到的是什么?后现代思想。
后现代思想其实它只是个名称,我们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后现代哲学家。我们现在归结它一个后现代头衔的哲学家其实都不会说自己是后现代哲学家,因为后现代已经被污名化了,比如说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这里面就是唯一说自己是后现代的,其实只有利奥塔。
这样一个情况的根源其实在于后现代它变得庸俗化了——我们提到后现代的时候,好像提到就是一种很流行的思潮,谁都可以是后现代一种反权威、多元主义、结构性差异。
这样一种差异,可以从一种女性主义到性少数的那样的群体,然后到后殖民主义。而后殖民主义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分,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从印度一直到埃及、再到非洲,就好像你越偏僻自己就越有一种现代的正当性。
但我这里是有些讽刺啊,我确实带有一些讽刺性在谈论这样的现象,但确实是这样。就说后现代变成一种政治正确了。尽管最开始后现代它代表的是一种激进性,但是在我们现在的25年内,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激进性已经被消解到了什么程度,被消解到了像齐泽克鼻炎这样十年前还算比较激进的思想家,你现在看他说话简直像个***。
我前面这样一些有些偏见式的讨论,其实就是想让各位注意到,其实思想的变化它不是按潮流来的——要按我们现在的潮流来的话齐泽克它已经不算什么了,拉康派的精神分析他们已经过时了;但是思想的变化,其实主要体现在它的那样一个内在强度上,而不是按照一个线性的时间的就怎么流行的方式来,或怎么怎么最正式正确的方式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思想的、那一种内部的强度过大导致的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形成的一团星群,就是在黑格尔他们的时代(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必定要被压抑的德国观念论的时代、浪漫派的一种狂飙图景)和德国古典哲学四个人(康德、费斯特、黑格尔、谢林)他们各自的一个思想发展,已经成了一种现在也很难再去理解和耗尽的思想资源。
而黑格尔他对这一点是有自觉的,所以他虽然会以一种看似是编年史和哲学史的方式去统摄前面的思想家,但是他自己其实是感受到了整个25年内在的一种思想差异性。那我们会看到这25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和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很像,就是形而上学被连根拔掉,从科学(Wissenschaft)的行列里消失。
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从费斯特开始,大家都喜欢谈Wissenschaft谈科学——康德开始就是一种能够作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导论,也就是说科学它代替了形而上学这样的名称,因为从康德开始,形而上学好像就成了一个要被批判的对象,成了一条死狗。但是我们要看到他批判的形而上学,其实只是一种旧形而上学,而这样一种旧形而上学就是经验化的经过了近代中介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也就是德国的学院哲学。
所以你们在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论里面区分了学院的哲学概念和世界的哲学概念。
学院的哲学概念,它是一种分科的方式,按一种哲学史的方式来做哲学;但是世界的哲学概念,他关注的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关注的问题会以变样的方式不断的在不同的时代出现。所以形而上学是有歧义性的。
在这个时期之前号称“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说已经被斩草除根, 从科学的行列里消失了。试想,什么地方还能够发出,或可以听到从前的 本体论、理性心理学、宇宙论,乃至从前的自然神学的声音呢?又比如,那 些关于灵魂的非物质性,关于机械因和目的因的研究,还能在什么地方得 到人们的关注呢?至于那些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其之所以被引用,也仅 仅是出于历史考据的目的,或为了让人超凡脱俗,净化心灵。这是一个不 容否定的事实,即人们对于从前的形而上学,要么对其内容,要么对其形 式,要么对二者同时失去了兴趣。当一个民族竟然认为,它的国家法哲 学、它的思虑,还有它的伦理习俗和美德,都变得没有用处时,这是一件值 得警惕的事情。同样,当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形而上学,当那个专注于自 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在这个民族里面不再拥有一个现实的存在,这至少 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
我们看到黑格尔他在谈形而上学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可以说是被逼迫的不得不专门来提到这样一种歧义性——传统被冠以形而上学之名的这样一个东西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其实区别在某种意义上不大。
我们现在所谓的后现代在黑格尔那里已经非常盛行,可以说常识学派休谟主义(一种意识的表征主义)和我们现代的心灵哲学,可以直接对应一些以反讽为主导的浪漫主义。而这样一种以反讽为主导的浪漫主义,也可以和我们的后现代思想直接对接。
黑格尔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所以我们的时代内在的是一种战争的状态,是一种思想的战争,而这样的一个战争状态,你可以说实际上只是黑格尔到现在的一个延续:黑格尔在那的时候就已经在和常识学派和浪漫主义进行战争了;他死了以后到我们现在为止,我们的战争转变了,转变成了一种对黑格尔的反对——你可以说这是浪漫主义的余波延续到现在,转变成后现代再反对黑格尔。
而黑格尔他自己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就是要反对浪漫派,他反对的可以说是一种庸俗化的浪漫主义,一种庸俗化的反讽犬儒主义。黑对犬儒主义的反对在现代还是在回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齐他自己其实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开始就在批判犬儒主义,他在批判一种庸俗化的后现代主义。
所以为什么黑现在会成为一条死狗呢?他为什么会一方面被一些学院派的哲学家征用,比如说被布兰顿、麦克道威尔他们征用,但另一方面就是许多后现代会反对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和黑他自己的一个思想处境是有关的,我们的思想处境还在他那样一个时代的支配、还在那样一个形而上学的战争状态当中,所以必定的我们无论是一种同盟的方式,还是一种对手的方式,亦或是一种理解对手的姿态,都会面对黑的论域。
现在黑格尔他就会开始谈到到底什么是形而上学。或者说什么是他这里谈到的被舍弃的形而上学,是从前的本体论理性心理学、宇宙论、甚至从前的自然神学?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学院派的概念被放弃了,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在理解本体论或理解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必须得确切地自己理解的到底是怎样的本体论、是怎样的形而上学。
因为康德开始到黑格尔批判的那样一个不再能够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本体论——就指的沃尔夫学派那样一个研究存在、存在作为存在这样一个范畴的含义了。而通过对这样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具体化出三种特殊的形而上学,也就三种作为分支的区域性的存在论:
即是理性心理学(就是对心理灵魂作为存在者的研究)、对宇宙世界作为一个存在者的研究和对上帝作为存在者的研究。而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最终都会和我们看到的对存在一般的研究关联在一起。
——所以你们会看到海德格尔他批判的本体神学,其实批判的也是德国学院派的形而上学。他海德格尔他虽然把本体神学扩大到了如此大的一个范围,就好像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和尼采都是本体神学。但真正的一个本体神学你看到其实是非常狭隘的一个学院派思想:他们把最高存在者自然神学的上帝与这样一种理性心理学意义上的存在者自我、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之为存在对存在者的奠基,也就是把存在者的大全奠基到最高存在者意义上的这样一个本体神学。
——海德格尔他对本体神学的一个批判,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没办法真的切中康德到黑格尔的一个发展,甚至无法切中近代哲学的发展。因为它的限定,其实原初的就是在这样一种旧的德国学院派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看到黑他就像现在我们提及一些新的思潮,比如什么认知科学、新实用主义和一些科学哲学里面对量子力场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之前的整个哲学已经失去意义了。但是我们要区分到底之前的哲学是什么。
比如黑这里会说:
试想,什么地方还能够发出,或可以听到从前的 本体论、理性心理学、宇宙论,乃至从前的自然神学的声音呢?又比如,那 些关于灵魂的非物质性,关于机械因和目的因的研究,还能在什么地方得 到人们的关注呢?
黑格尔以一种反问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就是没有人会再感兴趣研究这些了。因为整个科学的发展如此之迅速,对化学性、对生物的有机结构的一个发现,已经让我们不再会去研究什么“灵魂到底是非物质的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这样一个无聊的问题了。
所以上帝存在的证明,就历史而言就变成了一种修身养性——就好像为了表现你自己很有教养,我们还要去谈论一个上帝的本体论的证明,所以这里你们会看到上帝的本体论证明他一方面和旧的一般的本体论是有关的,因为本体论证明证明的是上帝是存在的,所以“存在本身是什么”这就是一般形而上学就本体论研究的。
同时,上帝存在证明它也可以是从宇宙论或自然神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比如说对上帝的宇宙论证明,阿奎纳五路或者一种自然神学证明——也就是说以一种自然自然神学的方式,从一种对自然意义上的道德的理解来证明就是上帝的存在这些已经没有人感兴趣,因为整个我们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对宇宙的理解、对心理学也就是对灵魂的理解,都发生了改变。
这样的一个批判其实是康德已经做出的。你看到康德他在二律背反里面就批判了宇宙论,而谬误推理部分批判的是理性心理学,其中先是理想部分反驳的是自然神学。所以他整个先验哲学,他的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可以说是对从前的本体论、对于存在一般的批判:存在,不再只是一个存在着的范畴——就是存在涉及到一个理性的设定,涉及到的就是整个先验主体性它的一个建制。
所以康德的先验哲学它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而有了康德的这样一个批判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再把旧形而上学当成一个科学了,这里是黑和康德的一个连续性。
所以你们看到这样的第一版序言,其实已经可以和黑格尔后来哲学全书那里的一个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对照起来阅读。
黑这里提到,
这是一个不 容否定的事实,即人们对于从前的形而上学,要么对其内容,要么对其形 式,要么对二者同时失去了兴趣。
这里黑格尔的态度逐渐变得模棱两可,这你会看到我们实际上不应该就完全的舍弃旧形而上学,尽管就事实而言大家已经对旧形而上学不感兴趣。
黑格尔很大程度上认为,就形而上学他对客观性的态度里面是有可取的一方面的,就他认为思维可以把握本质性(这点甚至导向了康德)。所以你们读这段序言的时候,不要以为黑格尔他好像在反问你就真的是说旧形而上学没有意义了,它的意思是旧形而上学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或一种真正的哲学思维来理解他想把握的本质,但是他对本质的这样的主张本身是没有问题,就是说他对于本质的信念其实是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后面这一段黑格尔他开始用了一种稍微有些反讽的方式来谈,
当一个民族竟然认为,它的国家法哲学、它的思虑,还有它的伦理习俗和美德,都变得没有用处时,这是一件值 得警惕的事情。同样,当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形而上学,当那个专注于自 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在这个民族里面不再拥有一个现实的存在,这至少 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
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就已经把它前面的一种看似是反讽的基调,一定程度上给消解掉。这里你们会看到,黑格尔他直接把形而上学问题和民族观念上的意思。
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里,就会看到黑格尔他精神哲学最后客观精神那里,出现了世界历史的概念。然后在世界历史那里开始了一个向绝对精神的转向,也就是在那里,黑格尔就指出了我们不是单纯停在一种对精神自己的自由可能性研究,也就是主观精神上;也不是在看精神如何在客观现实中把自由实现出来这样一个意义上来做哲学——就至少哲学不仅限定在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上,因为哲学它同时是绝对精神,或者说它总已经是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代表的就是形而上学。
所以说黑的态度,也就第一版序言里面的态度到后面还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形而上学本身其实不能被放弃:虽然旧形而上学已经不被感兴趣了,但是对形而上学、就是对纯粹本质的迅速的丧失是非常危险的。
这也就意味着,构成一个民族本质的我们,会看到民族是客观精神的一个概念。民族的本质其实就是和它的国家法是有关的:
我们会看到法哲学就是关于自然法和国家法的一个学说——一个民族,它的一个内在的本质,其实就表现在它的国家法,然后进一步的表现在世界历史那里,体现了它的风俗和它的道德方面。
这也就是整个客观精神里面的法的维度和伦理的维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本质,但是如果民族他自己不再关心这些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对它之所以成为民族的本质不再在意,这当然是件很奇怪的事。
当然我们现在不会觉得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彻底乱套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思想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你可以是润人,你可以是汉族家,你可以是别的任何任何任何的什么,然后你只要一进入到赛博世界的话,所有的标签你自己找就贴到头上,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在这里面**,而所有这些庞杂混乱的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争论其实都是在压抑一点,就是我们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一个本质。
当然这里很容易的就马上招来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就是我们都是后现代的时代了,谁还要关心自己的纯粹本质。
但是你们看了本质论就会知道黑格尔谈的纯粹本质,当然不是一个旧形而上学意义上不变的、永恒的纯粹本质。我们先不要给他上这样的头衔,因为我们知道本质实际上是什么本质,实际上就是自我差异化的一个运动,自我差异化的自己转变成想象的一个总以异化的运动。
这就是黑格尔他难读的地方,你们看到如果我们在不了解本质论的情况下,直接来读这一段的话,基本上马上会断定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最坏保守主义者。仿佛它的整个组织就是为了让一个民族去关心他自己的一个本质性的国家法,它的风俗和道路。
而这样一种解读,很明显的就会导致黑格尔变成一个原nazi主义者。实际上,我们理解它纯粹本质的一个意义就会看到。他这里的民族第一限定的不是德意志民族,第二,他的民族在客观精神的最后,是民族精神恰恰是要被一种更普遍的和形而上学有关的世界精神所超越的。
所以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其实是一种单纯后现代的态度,一种就是你不再关心形而上学、不再关心本质好像一切都可以用反讽来交接的态度其实最终导向的恰恰是一种民族主义,因为你对自己的本质的一种漠不关心、你对自己界限的一种漠不关心,其实恰恰会导向黑在客观精神最后揭示出的那样一个困境——就是你的所有言说,其实总已经是限定在了一种有限的国家法内在的界限内了,你本身对此界限其实没有自觉。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进一步的说法,刚刚看到黑格尔他认为形而上学既然和本质有关,也就和一种自我认知的精神是有关的,这也就意味着民族精神当它不再专心形而上学的时候,其实它不再专心他自身的那样的自我认知的方面,而对我们这些已经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人来说,我们知道他的这样的批判不是意味着他是一个原教旨意义上的什么本质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而是在于他看到这反而会倒向一个后现代式的困境。
这样的后现代式的困境,其实就是一种颠倒,就是你的一种认识正确其实直接颠倒成了一种对他者的遗忘、对自己的遗忘,所以他现在要提到康德哲学了,因为在开始上就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恰恰就是康德哲学。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们这里可以对照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因为第一种态度就是形而上学武断了,而第二种态度恰恰就是康德哲学。所以黑格尔这里马上提到
康德哲学的显白学说认为,知性不可以超越经验,否则的话,认识能 力就会成为一种只能产生出脑中幻象的理论理性;这就从科学方面为那 种放弃思辨思维的做法作出了论证。
这里的思辨的思维是很麻烦的,就你既可以理解成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思维,也可以看成是康德真正反对的、用实践的形式反对的那样一个思辨思维,但其实黑格尔他说的思辨和康德反对的那样的思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因为黑格尔的思辨恰恰讲的是一种实践精神和理论精神的统一,是一种自由精神,而这完全是符合康德精神的。但是康德他批判的思辩则是我们之前讲的那样一个旧形而上学单纯的要从理论方面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黑格尔他对康德的态度是有歧义的,是不那么好理解的。
这种通俗学说迎合了近代教育学的 喧嚣,迎合了这个仅仅盯着低级需要的贫乏时代;也就是说,正如对认识而言,经验是第一位的东西,同样,对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机敏精明 而言,理论认识甚至是有害的,毋宁说,各种练习和实践教育才是事关根本的、唯一有益的东西。——如此,当科学和普通人类知性携手合作,导 致形而上学走向消灭,一场奇特的大戏就上演了,人们看到一个有教养的 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正如一座在其他方面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庙宇里, 竟然没有至圣的神。一一过去,神学曾经是思辨神秘学和那种尚且居于 从属地位的形而上学的监护者,但现在它已经放弃了这门科学,用它来换 取情感、实践通俗的东西和博学的历史知识。与这个变化相对应的是,那 些孤独的人消失了,他们为自己的民族作出牺牲,隔绝于世界之外,只希 望沉思永恒者,过一种仅仅服务于这种沉思的生活——不是为了什么用 处,而是为了灵魂的福祉。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人的消失,和前面提到 的那些情况,就本质而言是同一个现象。——这样一来,当这些阴霾被驱 散,当返回到自身之内的精神不再苍白无力地专注于它自己,存在仿佛就 转化为一个更加开朗的繁华世界,而众所周知,没有哪一朵花是黑色的。
我们单纯看这一段话,我们好像觉得黑格尔他就是要要返回到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去证明思辨思维是有意义的,而康德哲学是没有意义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谈的思辨和汤德谈的思辨不是一回事。
但是黑格尔儿会认为康德他一旦被通俗庸俗化以后就完蛋了,就当时的时代以那些常识哲学为主的思潮,他们会片面的截取康德哲学的一些方面来反对康德哲学内在就有的和形而上学的有关的秩序,也就是和科学有关的秩序,毕竟康德他自己并不是单纯的要反对形而上学,他要建立一种科学的行为上去;但是一旦康德哲学被通俗化,以后整个行为上去好像就变得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种通俗学说迎合了近代教育学的 喧嚣,迎合了这个仅仅盯着低级需要的贫乏时代;也就是说
这里其实也就是说,黑格尔他认为整个他所处的时代是缺乏教养、缺乏教化的,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他会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面专门的提到一个笑话问题,就说精神现象学它作为一个导论,其实就是要把自然的意识,把那样一种通俗的被近代的教育学所沉浸的那样一个自然态度带上一种有效化的科学的观点。
我们再往回看,
正如对认识而言,经验是第一位的东西,同样,对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机敏精明 而言,理论认识甚至是有害的,毋宁说,各种练习和实践教育才是事关根本的、唯一有益的东西。
这也就是反驳当时的常识学派:就你要有常识,因为常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常识,你去搞那些所谓的哲学的话是害人的,你这里就是妨碍到我——无论这是你私人的生活情节、还是你仅仅是个陌生人,他也会觉得妨碍到公共社会的利益。(这里请结合最近事情联想下)
这里其实也有些类似于苏格拉底已经面对的一个问题。他苏格拉底在反对智者派的时候,其实他要面对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指控,引入新神的问题其实是次要的,因为本来古希腊就是多神教你,关键是你败坏了青年,你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共秩序。
所以黑格尔他会认为康德的学说或者说他的学说的一种庸俗化,迎合近代意识的一个需要。这样一种需要,就认为我们不要有哲学,我们不要有反思,我们要有一种常识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科学和常识的携手合作导致形而上学的崩溃。
这里很明显的,黑格尔的态度越来越的越来越指向了当时的那样一个常识主义了,也就是说常识对科学的败坏和对形而上学的舍弃。但是这里还是模棱两可的,就是说旧形而上学的崩溃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了解黑格尔那一篇短文就是《谢林与费斯特哲学体系的差别》的话,也会看到当时整个时代的需要就是要解决一个二元分裂,因为二元分裂的问题已经变得特别明显,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那样的统一性的主张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才出于这样一种需要的急迫性,必须要重新建立起一种形而上学。
但是黑格尔从一八零一年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就是说写第一版序言的一八一二年,大家看到都11年了。实际上问题根本没有改变,就科学没有被建立起来,
这里我顺便提一句,一八一二年的时候费斯特已经是在他的晚期阶段了。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费斯特的晚期知识学,基本上也就集中在了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也就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整个谢林的哲学高峰期都已经经过了,形而上学其实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科学还是没有建立——形而上学是彻底的崩溃了。
这里你会看到黑格尔他肯定是反对常识。就常识它和科学的一种狼狈为奸,导致形而上学彻底崩溃了,导致一个民族对他的一种本质性不不再去理解了:但是善恶的崩溃,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必然的。所以常识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就否定它,黑格尔在精神上学里面批判的这样一种自然态度它确实占据了一种支配性;而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真正的内在反驳他的话,我们得揭示出他的问题在哪儿,我们得把他带向一个科学的立场。
这一点是黑格尔他在整个哲学创作的时期都反复强调的,也就是说从一八零一年那样一个差异的论文,开始一直到一八零七年的精神现象学的出版,再到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到逻辑学的出版,黑格尔都在努力做这一点。
就是我们还是得把常识带向科学的立场,但实际上你要把常识带向科学立场的道路,对意识本身对自然意识来说是一种绝望。但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学问,我们才能真正的把它带上科学,从而让科学成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者反过来说让形而上学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
所以黑这里其实是痛心疾首的,
如此,当科学和普通人类知性携手合作,导 致形而上学走向消灭,一场奇特的大戏就上演了,人们看到一个有教养的 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正如一座在其他方面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庙宇里, 竟然没有至圣的神。
这里其实却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是认为黑这里说的就是一种肯定的说法,也就是说民族就是没有形而上学。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黑格尔他其实是在只出于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不可能是没有形而上学的。我我们现在来判断黑格尔到底是在哪个意义上谈论形而上学,就得通过它后面这一段:
过去,神学曾经是思辨神秘学和那种尚且居于 从属地位的形而上学的监护者,但现在它已经放弃了这门科学,用它来换 取情感、实践通俗的东西和博学的历史知识,
这也就是说神学伴随着形而上学的一个崩溃他自己也退化了,退化成了一种日常的说教,只是和一种情感、和单纯历史的见闻有关。
与这个变化相对应的是,那 些孤独的人消失了,他们为自己的民族作出牺牲,隔绝于世界之外,只希 望沉思永恒者,过一种仅仅服务于这种沉思的生活——不是为了什么用 处,而是为了灵魂的福祉。
这里的意思也就是形而上学家他被隔绝于世界之外,是因为形而上学这个学科本身或者说这样一个思想本身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这部分人也就消失了。所以从这样一个现实层面上来看,即神学的庸俗,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基督教的世俗和形而上学的蜕变。
形而上学的消失,实际上就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这样的旧形而上学的时期是一体两面的,是一个现象。那这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它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发生了,但是这样一种发生不代表就应当是如此。所以黑格尔虽然批判旧形而上学,但他始终会认为旧形而上学要坚持的那样的态度本身是不应该被直接否定的。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展演活动在凤翔学校顺利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展演活动在凤翔学校顺利开展
 信阳市市文广旅局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放权赋能培训会召开
信阳市市文广旅局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放权赋能培训会召开
 淮南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公布
淮南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公布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在榆林成立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在榆林成立
 定了!在郑州举办的2022中国非遗年会延期举办
定了!在郑州举办的2022中国非遗年会延期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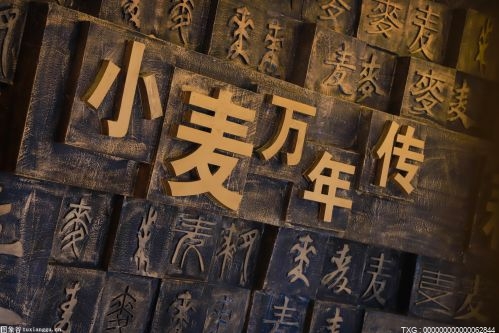 喜讯!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技艺”被列为省级非遗
喜讯!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技艺”被列为省级非遗
 从“非遗进校园”到“非遗在校园”!广东发布20个优秀案例
从“非遗进校园”到“非遗在校园”!广东发布20个优秀案例